寒风中的乡愁
□ 蓝江安
行道上的银杏树叶已经泛出焦黄色,纷纷洒落,像是不断向路人倾诉严冬的到来。
昨夜,寒风阵阵吹过。半夜醒来,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近听,那风拍打着小街上的路灯盖,发出“啪啪”声响;远听,那风撕扯着寻常百姓家的雨棚,发出“哗哗”声响。在不远处的一家,孩童的哭声越来越大,似乎要与大风比个高下,母亲轻柔摇晃的哄睡声也似乎溜进了双耳。看来,这个夜晚又成了不眠之夜。我索性打开灯,端上一杯红酒慢慢品尝,思绪不由得飞回到故乡的寒夜。
故乡的老屋是穿斗式结构,后排墙壁由竹篱笆涂上黏土构成。故乡的寒冬远比蜗居在城里寒冷。屋后坡上是遍野的竹子,它们经不住寒风的折腾,有的齐腰折断,有的倒伏在小树上,绵绵缠缠。老屋年久失修,寒风就会从竹篱笆里吹进,冷飕飕的,我们几兄妹不由得裹紧了被子。这时,母亲会习惯性地一一检查我们的御寒情况,不放心地理顺了每个人的被子,然后又翻箱倒柜拿出棉衣、棉被为我们加厚防寒。
第二天黎明早早醒来,母亲待我们吃完早饭后,会一个人默默地往篱笆上补上黏土。家里缺乏主劳力,我们还小,父亲又在外地当工人,母亲便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杀鸡、耕田等男人做的活儿她也不得不亲力亲为。岁月在她额头上刻下了与年龄不相称的皱纹,窈窕的身子变得有些佝偻,黢黑的头发中夹杂着几根很显眼的白发。母亲的艰辛孩子们不懂,因为孩子们的心智还不成熟,不懂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南方的下雪天很少。偶遇瑞雪年,我们几兄妹便组织四合院内的十多个孩子打雪仗,用冻僵的小手抓一把雪放进嘴里,味儿淡淡的,吐出来,然后又抓一把扔进童伴的颈窝或者放进他们的心窝,开怀大笑,一哄而散。我们学着《智取威虎山》的动作,由我主演座山雕,解放军方有侦察连、卫生队和突击队,“八大金刚”全由大个子主演。孩子的模仿力强,别看我们年纪小,演起来竟然像模像样。就拿我而言,把座山雕狡猾而又愚蠢、多疑而又自负的性格演绎得惟妙惟肖。不过,“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成功演绎的背后可吃尽了苦头:作为影片中最大的“坏蛋”,我自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于是乎,雪球天女散花般朝我飞来,就连卫生队的女战士也不忘朝我扔雪球。如果雪下得少,他们就抓泥巴坨扔。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叫春花的小丫头竟然抓起一把牛粪扔到了我的新衣上。
我被“革命战士”打成了筛子。回到家里,恰好父亲探亲回来,见我模样,他先是冷笑了两声,接着对我实施最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打屁股。
孩子们的忘性大。又一年下雪天,我们和临村孩子商议上演《红灯记》。在物色叛徒王连举演员时,我自告奋勇说非我莫属,完全忘记了饰演座山雕的悲惨遭遇。不过这次我吸取以前被动挨打的教训,开始进行自卫还击。打得正面人物“李玉和”鬼哭狼嚎,打得“李铁梅”逃之夭夭,完全弄反了内容。最后演戏变成了打雪仗。
寒风把我们吹送入春节。我们快乐地穿上新衣裳,拍“豆腐干”“偷十点半”。我们跳绳,“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我们还偷偷将家里的食物拿到竹林里“过家家”,学着大人的样子,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孩子们的世界总是纯真的甚至幼稚可笑的。
寒风年复一年吹着,将我们吹送到青少年,将我们吹送到青壮年,我们感受到知识的不够用。于是,我们挑灯夜读,拼命把那荒唐岁月里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曾记得,为了脱掉“草鞋”穿上“皮鞋”,我发扬“头悬梁、锥刺股”精神,在竹林里、在山泉边、在煤油灯下埋头苦读。尤其在酷暑的夜里,母亲陪读,打着蒲扇为我驱蚊,那一摆一摆的风中寄寓着望子成龙的情愫。
寒风将我吹送到老年。我没了童年时的纯真,没了青少年时期的闯劲,更没了壮年时的成熟与拼搏精神。与此同时,返璞归真的思想愈来愈强烈,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乡愁,便积郁难眠。其实,乡愁就像年复一年都要来临的寒风一样,越吹越大,越吹越远。
(作者单位: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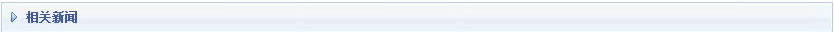
- ·买网络电话软件赚钱?原是新型传销2016-01-07 10:38:18
- ·“清零”公司财产 六旬“老赖”被判刑2016-01-07 10:37:59
- ·在贴吧发布不实信息 女子被批评教育2016-01-07 10:37:35
- ·迷恋网游缺钱花 男子抢劫落法网2016-01-07 10:37:23
- ·87岁老太告七子女 法官执结案子挽回亲情2015-12-24 14:31:46
- ·自贡女老板澳门旅游 被人盗刷40多万元2015-12-24 14: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