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 岳雨禾
我的老家,曾是一所无需锁钥的院落,坦然地敞在川东北大巴山的皱褶里。院坝前的老腊梅和柿树,以及屋前大冬水田后面那口敦实的水泥储水缸,便是它全部的门楣与界碑。后来,楼叠起来了,栅栏也砌起来了,三层的小楼镶着锃亮的铝合金窗,围着雕花的铁艺栅栏,气派而又沉默。只有当我的目光,掠过那冰冷的栅栏,固执地落向记忆的原点时,那株腊梅、那树柿子、那口储水缸,才会带着它们各自的温度与光亮,悄然浮现,为我勾勒出老家最初的、敞开的轮廓。
腊梅的香,是老家冬日里一封寄给过路人的、没有落款的请柬。
那时的院坝没有栅栏,泥土地被家人的脚步夯得坚实光亮。那株腊梅便立在院坝边,瘦硬的枝干有一种清矍的骨气。一入深冬,繁密的粉红便毫无征兆地炸开,像沉默了一整年的人,突然倾吐出满腹星辰般的密语。香气是清冽的,不带一丝甜腻,是冷的芬芳,能钻透凛冽的空气,直抵肺腑。
最动人的景致,属于那条从门前蜿蜒而过的乡间公路。那条路上的车不多,多是风尘仆仆的私家车,或是突突作响的拖拉机。但几乎每一辆车行至此处,都会不自觉地放缓速度。我见过摇下车窗深深吸花香的司机,见过跳下车来,举着相机,小心翼翼寻找最佳角度的旅人,更有附近的农人,担着柴禾或菜蔬,径直将担子放开,走到树下,仰着头看上好一阵,仿佛在上一堂虔敬的晨课。
这株腊梅,成了这段乡间公路上一个心照不宣的驿站。它不属于任何人,又仿佛款待着所有人。它以毫无保留的盛开,将我们私密的院落与广阔的外部世界温柔地连接起来。那芬芳是流溢的,目光是共享的,那一刻的驻足与赞叹,是公共的。老家的慷慨与好客,第一次在我心中有了形状——那是一株树,主动将最美的一面,赠予每一位偶然途经的生命。
柿子的红,是秋天为老屋独家签署的、一份甜蜜的封印。
屋前的柿子树,生得随意,枝桠歪斜,却异常慷慨。秋霜一降,叶子便簌簌落尽,只剩下满树沉甸甸的果实,由青转黄,最终酿成一片酡红。那红,不像枫叶那般飘忽,是实心的、厚重的,像无数盏被点亮的、圆滚滚的小灯笼,牢牢系在枝头,照亮日渐萧索的庭院。
关于柿子,我们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许提前采摘!我们眼巴巴地守着望着盼着,看着它们在秋风里一日日软化,那层仿佛镀了蜡的表皮,渐渐变得温润而透明,能窥见内里流动的、蜜一般的瓤。外公总在某个有阳光的早晨,用长长的竹竿,末端小心地系上网兜,将那熟到极致的、几乎要自行坠落的、红得发光的果子摘下来。它们被轻轻放在铺了稻草的竹筐里,供家人美美享用。
真正的仪式在品尝时。必须等到它“耙”透了,软得无从下手,只得在顶端撕开一个小口。顿时,一股清甜的香气先于滋味涌出。俯下身,就着那缺口轻轻一吸,冰凉、滑糯、甘醇的柿肉便涌入喉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涩味,只有阳光与秋风凝练成的、纯粹的甜。这甜,是耐心等来的,是时间赠予守约者的奖赏。它不像腊梅的香那般外放,而是一种内敛的、仅供家人享受的富足。那满树红灯笼,映着老屋粉红的瓦,是家园安稳、仓廪充实的无声宣告。
储水缸的泽,则是夏日赠给我们四个孙女的、一座流动的乐园。
那是一口巨大的水泥储水缸,浑圆,粗粝,全年无休蹲守在水田旁的墙角。它盛放的并非琼浆玉液,而是从井里打上来的、最普通的清水。然而,在童年的宇宙里,它却是快乐的源泉。漫长的暑假,炎热的天气,当午后灼人的阳光将大地晒得发白,我们便盼望着期待着傍晚五点的到来。那时的阳光已成余威,恰好将曝晒了一天的清水,烘得温热。外婆便会笑着宣布:“水热了喽!娃娃们可以泡澡喽!”
“这件衣服是我的!”
“我要站在最里面!”
“我要泡泡机!”
四姊妹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这便是一天中的高潮。储水缸足够大,我们四姊妹各据一方,像四只被温水浸泡着的、快活的小青蛙。缸壁沁着石质的、幽幽的凉意,而水则是恰到好处的暖,将浑身的黏腻与疲惫一丝丝抽走。我们说着、游着、笑着、乐着,讲着学校里的八卦趣事,比赛谁能憋气更久,看谁吹的泡泡最大,想象着天空中的云朵像棉花糖还是……水花溅到脸上,缸壁上滑腻的青苔蹭着后背,仰头是渐渐染上绯红的天空。这口粗笨的大储水缸,用它朴素而包容的胸怀,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微型天堂。
对于老家,梅香是“馈赠”,赠予陌路,勾勒出老家与世界最初的、开放的联结;甜柿是“守候”,留给家人,沉淀下家园内部绵长而安稳的幸福;水缸是“共享”,属于玩伴,封存了童年最恣意烂漫的肉体欢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心中“老家”的完整意象:它既是向外敞开的、慷慨的,也是向内凝聚的、甜蜜的,更是充满生命本身那种粗粝而蓬勃的、欢愉的。
如今,当我站在那栋簇新而沉默的三层小楼前,面对着那扇需要钥匙才能打开的、冰凉的铁门,我忽然明白,老屋的消逝,并非仅仅是一所建筑的更迭。那株邀约过客的腊梅,那树点亮家园的柿子,那口盛满童谣的储水缸,它们所承载的那种开放、等待与共享的“生活仪式”,连同那片可以自由奔跑、无界分享的物理空间,已一同被砌进了高高的栅栏之内,被封存在了一个名为“过去”的琥珀里。
我的外公外婆,在这安静、安全的新居中,日复一日地安度晚年。他们不再需要为一树腊梅而欣喜,为一筐柿子而操心,为孙女们的洗澡水而忙碌。他们的岁月,被安放得妥妥帖而寂寞。
那株梅、那树柿、那口缸,是老家的“三不朽”。它们在我的心中站成一个永恒的三角,支撑起一片永不倾颓的天空。
在那里,老家从未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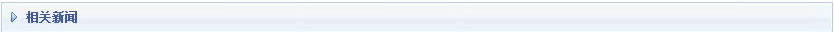
- ·法治四川客户端广告代理招商公告2023-04-04 17:03:40
- ·87岁老太告七子女 法官执结案子挽回亲情2015-12-24 14:31:46
- ·自贡女老板澳门旅游 被人盗刷40多万元2015-12-24 14:31:29
- ·盗贼拒捕 竟抽出猎刀砍向民警……2015-12-24 14:29:42
- ·广元:加强“庭所”规范化建设2015-12-10 15:56:59
- ·犍为:办案区升级改造工作获肯定2015-12-10 15:5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