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墙村到赵家渡(二首)
□ 胡中华
土墙村
泥土夯进骨缝,土墙便站立。
它围住桃李、犁耙与牲口的呼吸,
围住晨昏、婚丧与日子缓慢的沉积。
当葵花形的太阳用土黄色言语,
说这里曾是一座安稳的殿堂。
墙内,黎明是颗浑圆的大橙子。
狗吠如温热的农谚传来,
槐花的影子在院里踱步,
模仿母亲弯腰的劳作。
黄昏暗自惊喜——
嫂子倚在门框,胸襟微微起伏,
仿佛胀满了月光的乳汁。
墙懂得坚硬的事物:
山岩、老木、祖先弓下的脊梁。
墙也听见,墙外——
挖机啃噬梯田,
钻头掏空山腑,
推土机压熄了最后一柱
笔直的炊烟。
小径渐渐淡去了足迹,
溪水哑然。墙在高速路旁
矮了下去,被荒草与藤蔓
吞咽,漫出大片大片的绿与寂静。
墙倒下了,依旧是土。
我蹲下身,抚摸散落的土坷,
忽然明白:所有遮蔽
终将袒露,所有闭合
都是敞开。墙从未真正倒下,
它只是换了一种姿势,
匍匐在大地——
像根,在风中,继续站立。
赵家渡
在赵家渡,不再为跌价的砖瓦懊恼。
涪江摊开右岸的绿,收留我。
有太阳的黎明从东津沱升起,
有月亮的黄昏向龙游寺降落。
我从遮蔽风雨的格子出发,
从大地上唤作“上境”的蜗居中出走,
穿过丢失红绿灯的路口,遁入
山的影、水的纹,与半醒的雾。
在这里,我学习爱——
爱刚绽放的,也爱将枯萎的;
爱一整棵树,也爱它递出的落叶;
爱振翅的,也爱低鸣的;
爱所有未名之死,与复生。
危险的美,依然美得危险,
像暗藏其刺的玫瑰。
风中有残香,有体温,
有从黎明铺到黄昏的微光。
江水含住日月、碎星与灯火,
也含住身后列车穿行,如穿隧洞。
门前,流水洗我,如洗滩石。
肉身与光阴互研,彼此成全。
星辰暗换穹顶,草木枯荣呼吸。
我立于此间,任星火漏入江心,
不问浮沉,只觉风从指间,
静静穿过,如穿过一句未竟的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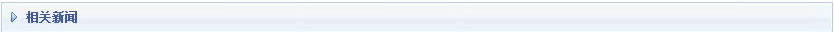
- ·法治四川客户端广告代理招商公告2023-04-04 17:03:40
- ·87岁老太告七子女 法官执结案子挽回亲情2015-12-24 14:31:46
- ·自贡女老板澳门旅游 被人盗刷40多万元2015-12-24 14:31:29
- ·盗贼拒捕 竟抽出猎刀砍向民警……2015-12-24 14:29:42
- ·广元:加强“庭所”规范化建设2015-12-10 15:56:59
- ·犍为:办案区升级改造工作获肯定2015-12-10 15:5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