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味
□ 钱薇伽
元旦小假,我回重庆照料动手术的母亲。守夜至天明,母亲催我回家歇息。归途清冷,我在家楼下那间寻常的早餐铺前驻足。铺子卖的是豆浆油条、稀饭包子,我总喜欢到这家来——只为久违的糯米团。
那是山城里渐渐隐没的古早味道,童年时最常见的早餐之一。一勺热气氤氲的糯米饭铺在洁净的棉布上,放上一截刚炸好、金黄油亮的酥脆油条。撒一把白糖与芝麻碎,棉布迅速收拢,一拧一裹间,一个两头尖、中间鼓的糯米团便成了形。交到客人手里前,还要在磨得细细的黄豆面里滚上一圈,两头再蘸上晶亮的白糖。趁热咬下去,糯米的软、油条的脆、白糖的甜、豆粉的香,在齿间交织成一场温柔。
可这一次,我刚咬下,心便凉了半截。糯米冷硬成坨,油条黏牙而寡淡,像被生活磋磨过的牛皮糖。没有甜意,亦无香气,它只是一团被时间遗忘的、冰凉的糯米。
有些哭笑不得。记忆里,糯米团是照进灰暗童年的一缕暖光。若考试考得好,妈妈会多给点钱,让我在上学路上买个糯米团。校门口摆摊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她总是笑眯眯的,给我的糯米团永远裹得紧实,两头沾满厚厚的白糖。滚烫的甜糯足以融化我少年时被孤立、被忽视的冰霜,在贫瘠岁月里悄悄酿出温暖的一米阳光。
这份通过食物传递的慰藉,也延续到了下一代。儿子从小学棋,每周末大清早就要赶去棋校。有一次,我忽然记起棋院后街有家老面馆卖传统的成都蒸蒸糕,便带他去尝。他踮脚望着操作台,只见师傅用蚌壳勺舀起米粉,填进麻柳木雕成的模具,再架到高压锅的蒸汽口上。待米香飘出,师傅麻利地塞进一勺红豆沙。脱模的蒸蒸糕莹白如玉,中间一点豆沙嫣红,热气腾腾地递过来。大米与糯米交融的柔软,豆沙的绵甜,让孩子眼睛一亮。从那以后,孩子每周去棋校的动力,从“学棋”换成了“吃糕”。哪怕偶尔迟到,他进教室前也不忘回头,认真叮嘱我:“妈妈,记得买蒸蒸糕,我下了课要吃。”
可童年似乎总擅于在我们转身时悄然改换面貌。某个暑假过后,我们兴冲冲再去,店招已换成明晃晃的炸鸡招牌。新店主热情招呼,我们却相视无言,竟然落荒而逃。至今儿子仍会念叨:“蒸蒸糕太好吃了。”
变化永远是这个世间的恒常,虽然我们怀念曾经的美味,但时代如江河奔涌,一味守旧,终将被冲散。就像那失了温度的糯米团,空有形式,丢了魂魄。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固执地停在原地,而是保留精华,创新形式,在碰撞中产生新的美好。比如新派的融合菜里,麻婆豆腐混合意大利面,麻辣小龙虾铺满披萨底,茅台和咖啡碰撞出新的味型;传统小吃也在悄然新生——烧麦裹进了芝士与蛋黄,冰粉撞上了咖啡与椰浆,巧克力粉洒满麻薯油条。变,是生存的智慧,也是活力的源头。
万变之中,有些东西终究需要留住。两天后,朋友告诉我另一家糯米团不错,恰巧在幼时的幼儿园附近。我寻去,在糯米团入口的一瞬,这就对了。糯米软热,油条酥脆,白糖在舌尖轻轻化开。我这才意识到,油条出锅必须立刻裹进糯米里,再包上棉布,可以让油条免受氧气的“摧残”,这样的糯米团才是香糯包裹酥脆。这家糯米团更是创新,包裹的不是油条,而是油条颗粒,口感比油条更加香脆。结账时,手机扫过绿色小方框,“滴”的一声,我不禁莞尔,这才是与时俱进。
握着手心温热的糯米团,我走过晨光初醒的街道。坚守从不是拒绝所有新意,而是护住核心——对滋味的敬畏,对手艺的笃信。在这个新旧交织的时代里,守得住本源,才容得下新章。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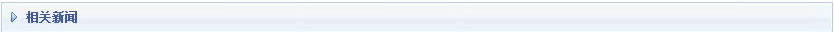
- ·法治四川客户端广告代理招商公告2023-04-04 17:03:40
- ·87岁老太告七子女 法官执结案子挽回亲情2015-12-24 14:31:46
- ·自贡女老板澳门旅游 被人盗刷40多万元2015-12-24 14:31:29
- ·盗贼拒捕 竟抽出猎刀砍向民警……2015-12-24 14:29:42
- ·广元:加强“庭所”规范化建设2015-12-10 15:56:59
- ·犍为:办案区升级改造工作获肯定2015-12-10 15:56:59
